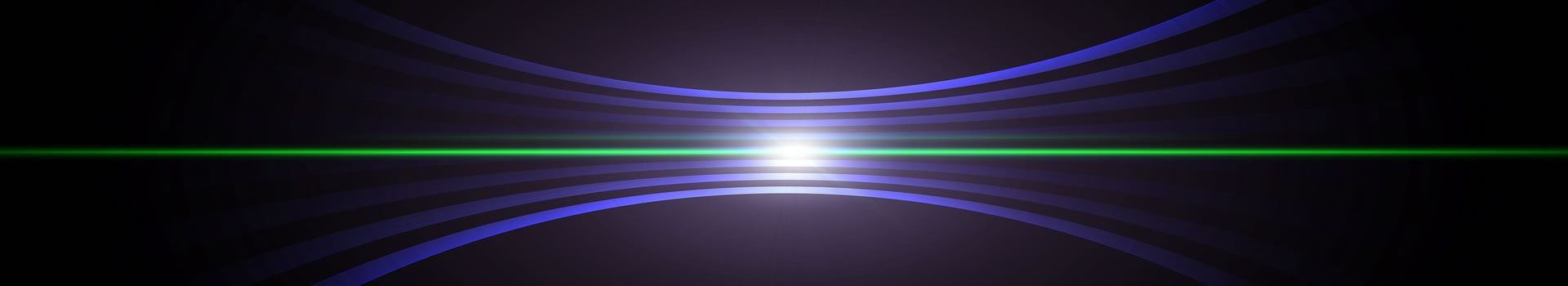
一万两千块,买一个“万一”。
这是王建军给出的理由,当他把三个月跑运输、扛钢筋换来的血汗钱,交给了那个叫做“明日之光”的夏令营时。机构的视频里,孩子们在苍山的草地上追逐蝴蝶,老师说“草木气能通感官”。他想着,万一,那个只会说“要”和“不要”的八岁儿子,能开口喊他一声“爸”呢?
这个“万一”的代价,是四天三夜后,在二十米深的山涧里,他看到了儿子小小的、冰冷的身体。
那个出发前塞好的、妻子亲手织的小毛衣,被溪水泡得发胀,敞在行李箱里。
所谓的“自然疗愈”,最终以最残酷的自然方式,画上了句号。
北京的出租屋与苍山的风
为了给一凯治病,这个家早已被掏空。王建军和妻子在北京租了间破旧的小屋,妻子全职守着康复机构,他则白天开货车,晚上去工地加夜班。
他曾对人说,只要儿子能多看他一眼,什么苦他都能吃。
生活被压缩到只剩下一个目标:让儿子的世界打开一道缝。
一凯的世界很小,小到连自己穿衣都得人帮忙,小到去年在小区玩滑轮车跑丢,被找到时,只是蹲在马路牙子上安静地数着车轮。
他不会呼救,甚至不会说一个完整的句子,急了只会去扯别人的衣角。
所以当“明日之光”许诺一个“草木通感官”的奇迹时,王建军赌上了全部。
姥姥劝他再想想,他红着眼坚持。
他把对儿子未来的所有想象,都寄托在了那片他从未踏足过的、遥远的苍山。

扳手落地的声音
变故的信号,是“当啷”一声。
八月九日傍晚,王建军正在给货车换轮胎,姥姥的电话打来,说一凯在夏令营走丢了。他手里的扳手应声落地,砸在地上,也砸碎了他所有的侥幸。
他连夜赶到大理,迎接他的是四个老师苍白的脸。
七个孩子,四个老师,偏偏是那个最不会求助的一凯,消失在了山里。
“他连‘help’都不会说”,王建un蹲在营地边,指甲抠进湿润的泥土里,一遍遍重复着。
他兜里揣着儿子的诊断书,那张纸的边角很快就被苍山的雨水浸得卷了起来。
饼干和带血的手
八月十日凌晨三点,第一支搜救队进山,王建军跟在最前面。
他没合过眼,头灯的光柱在浓雾和雨幕中摇晃,他手里攥着儿子穿了三年的旧凉鞋,走几步就用嘶哑的嗓子大喊:“凯凯!
爸在这!”

救援队划分了区域,他抢着去了最难走的北坡。
那里的草比人还高,雨后的山石湿滑无比。
他滚下过山坡,手掌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,爬起来,他只是拍拍土,继续喊:“凯凯!看爸给你带饼干了!”他口袋里装着一凯最爱吃的草莓味饼干。
同行的队员劝他歇歇,他摆手拒绝,“我儿子怕黑,我得喊着他,他才敢出来。”
这四天三夜,他的喊声几乎没有停过,从充满希望到渐渐绝望,最后只剩下机械的本能。声音撞在树干上,散在风里,却再也没能等来一声回应。
那颗攥紧的奶糖
搜救进行到第四天下午,王建军正沿着清碧溪往下游寻找,上游传来了消息。他疯了一样往回跑,脚底被尖锐的石头硌得生疼,却毫无知觉。在那个二十米深的山涧边,他看到了终点。他想冲下去抱起儿子,被队员死死拦住。
后来,他在救援队的微信群里,打了很多字,又一个个删掉。
最后只发出去一句:“这几天大家辛苦了,代一凯谢谢各位。”群里有家长在痛骂机构失职,他没有参与讨论。他只是拿出手机,用袖子擦了擦屏幕上一凯的照片,照片里的孩子,眼神依旧飘向镜头之外。
收拾遗物时,他在一凯的裤兜里,摸到了一颗被攥得皱巴巴的奶糖。
那是出发前,他亲手塞给儿子的。“这孩子,啥都不会,就知道攥紧好吃的。”王建军低声说着,小心翼翼地把糖纸铺平,夹进了自己的钱包。钱包里,还有一张全家福。
结语
悲剧发生后,夏令营的资质和老师的责任问题,正在接受调查。人们愤怒于这类机构打着“锻炼孩子”的旗号,却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。
去年就有夏令营出事,孩子崴脚在山上苦等两小时。
这些血的教训,似乎总也换不来行业的警醒。
王建军没有再多说什么,他只是想告诉和他一样的家长们:“别信那些花哨的词儿,孩子要的不是大山,是你在他身边,一步都别走开。”
苍山的雾最终还是散了。王建军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,陪着儿子下山。
他走得很慢,时不时会停下来,对着身后轻声说:“凯凯,爸带你回家了。”
山风穿过林间,呜呜作响,像是孩子一声模糊不清的回答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