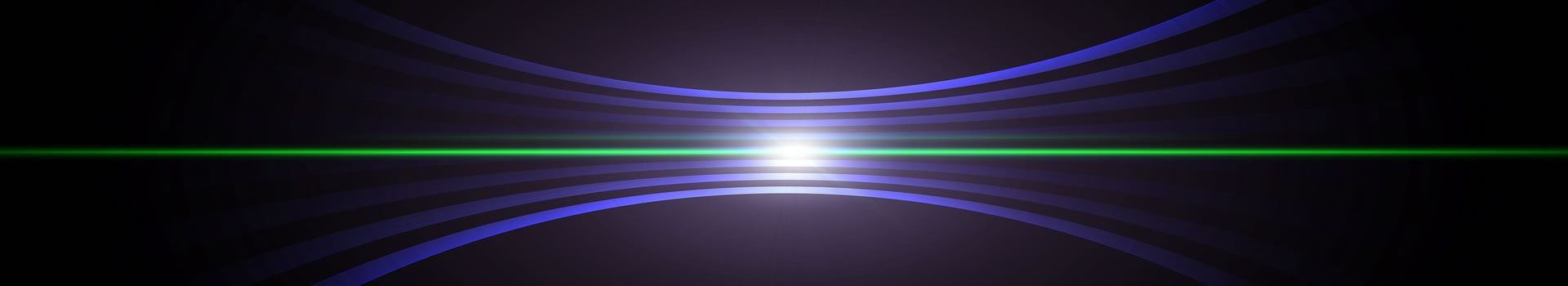

“王建国,你赶紧把那破窗户关上!熏死人了!”
张桂芳的嗓门穿透了傍晚厨房的油烟。
老王正蹲在阳台上,就着最后一点天光,使劲刷着一块汽车脚垫。泡沫飞溅,但那股若有若无的腥臭味,还是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。
“刷刷就干净了!”他闷声回道。
“赶紧扔了!”张桂芳拿着锅铲冲出来,“从你买回那辆破车,家里就没一天安生!一股死鱼烂虾味!你闻闻你身上!”
老王没吭声,手上的力气更大了。
他刚退休,图便宜从二手市场淘了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,本想着接孙子、拉点东西方便。
可这车,打第一天开回来,就透着一股邪门。
那股味道,说不出的怪。
不是香水,不是烟味,也不是单纯的霉味。它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,又被强行掩盖住,丝丝缕缕地往外渗。
老王心里堵得慌。他这辈子最重脸面,被人说贪便宜买了辆“味儿车”,比骂他还难受。
“我就不信这个邪!”他咬着牙,刷得更用力了。
01.
王建国在老钢厂家属院长大,干了一辈子机修,刚退下来三个月。
人一闲,就慌。
儿子儿媳在城那头上班,小孙子刚上小学。老王寻思着,买个车,风雨无阻接孩子,周末还能拉着老伴去趟郊区。
“买新的?那不是烧钱吗!”他对手艺极其自信。
“我这手艺,修车厂的师傅都得叫我声老师傅。二手车,我一眼就能看穿!”
张桂芳拗不过他。
老王揣着攒了半年的退休金,在城郊那个龙蛇混杂的二手车市场转了整整三天。
最后,他看中了这辆银灰色的面包车。七成新,跑了八万公里,价格比市价低了快两万。
“哥们,这车,原车主急着用钱,抵押的。手续齐全,您放心。”那个染着黄毛的销售拍着胸脯。
老王里里外外检查了三遍。
他趴在地上看了底盘,拧开机油盖闻了闻,又发动了车,仔细听发动机的声音。
“没杂音,底盘也干净,就是这车里香水味浓了点。”老王皱眉。
“哎哟,前车主爱干净,总喷清新剂!”黄毛笑得露出一口黄牙。
老王图这个便宜,又自信自己的技术,大笔一挥,车开回了家。
车开回老家属院,倒是风光了一阵。
“老王,行啊,鸟枪换炮了!”
“这车宽敞!比老李头那小轿车实用!”
老王得意洋洋,把座椅擦得锃亮。
可好景不长,三天后,那股浓烈的廉价香水味散了。
一股怪味,开始升腾起来。
就像张桂芳骂的,一股死鱼烂虾味。
张桂芳第一个发难。“你开这车去接孙子,孩子同学不得笑话他?孩子闻这味儿,不得生病啊?”
孙子是老王的命根子。
这话戳心了。
老王第二天就买了十几个竹炭包、四大个柚子皮,塞满了车厢的角角落落。
没用。
那味道黏糊糊的,扒在座椅和内饰上,怎么都去不掉。
家属院的风言风语也起来了。
“老王那车,是不是泡过水啊?我闻着那味儿不对。”
“我看着像事故车,不然能那么便宜?”
老王嘴上不说,心里憋着一股火。他一辈子的精明,不能栽在这辆破车上。
他开始魔怔了。
每天早上五点,天不亮,他就提着水桶去擦车。
擦完一遍,他就趴在座椅上,贴着缝隙,像警犬一样使劲闻。
他必须把这个味道的源头找出来。
02.
老王决定去找那个黄毛销售。
“哥们,这车味儿不对,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”
他开着车,凭着记忆摸到那个二手车市场。
市场还在,那个挂着“诚信车行”的铺子,却拉上了卷帘门。
隔壁修车铺的师傅磕着瓜子,斜眼看他:“找小黄啊?”
“对,他不干了?”
“嘿,”师傅乐了,“前两天就被警察带走了,说他们卖的车手续有问题,净是些抵押黑车。”
老王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手心冒出冷汗。
他一言不发,钻回车里。
他开着车往回走,心里七上八下。这车,不会真是个“黑车”吧?万一查到自己头上,这辈子的清白不就毁了?
他把车停在路边,找出购车合同和车辆登记证。
登记证倒是真的,车牌也能对上。他用手机上网查了,状态也正常,不像是被通缉的。
他松了口气,但随即又烦躁起来。
手续没问题,那这股味道,就纯粹是“质量问题”了。
这天下午,他去接孙子。
小孙子刚拉开车门,就捏住了鼻子:“爷爷,你车里怎么这么臭啊!比上次还臭!”
老王尴尬地僵在原地。
“是不是...是不是爷爷昨天买的榴莲忘在车上了?”他强行解释。
孙子嘀咕着:“才不是榴莲味...是...是臭肉味!”
孩子的话最伤人。
晚上,张桂芳下了最后通牒。
“王建国,这车你要是再弄不干净,明天就给我卖了!听见没有!”
“卖?”老王跳了起来,“我刚买回来!这一转手,亏一万多!你当我的退休金是大风刮来的?”
“亏钱也比熏死强!”张桂芳把筷子拍在桌上,“你那点退休金,别都折腾在这破铜烂铁上!我可不想孙子坐这‘味儿车’!”
经济压力和家庭矛盾,把老王逼到了墙角。
他一夜没睡好。
凌晨四点,他爬了起来。
他不能卖。卖了,他就成了全家属院的笑话。他王建国一辈子的英明,就全毁了。
他拿着手电筒,又钻进了那辆面包车。
竹炭包已经吸饱了水分,软塌塌的。
柚子皮也干了,混在那股怪味里,闻起来更恶心了。
老王把所有东西都清出去,趴在地上,一寸一寸地闻。
驾驶室...没有。
副驾驶...没有。
后排...
他停住了。
味道最浓的地方,好像是...第二排的右侧座椅。
那是一张独立的座椅。
老王使劲按了按坐垫,又拍了拍靠背。很结实。
他把手电筒调到最亮,贴着座椅的缝隙往里照。
黑乎乎的,什么也看不见。
但那股味道,就是从这里钻出来的。
03.
接下来的两天,天开始转热。
气温一升高,那股味道彻底爆发了。
不再是若有若无的腥臭,而是一种...腐烂的、带着铁锈的甜腥气。
老王在车里待五分钟,就觉得头晕眼花。
他不敢开窗,怕邻居闻见。
他也不敢开空调,一开内循环,那味道能把人顶个跟头。
他把车开到了熟人介绍的汽修厂,想让师傅帮忙拆开看看。
“王师傅,您自个儿就是行家,还信不过我们?”洗车工小李笑着说,“我给您做个深度清洁,再来个臭氧消毒,保证没味儿!”
老王犹豫了一下。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拆车,万一拆开了啥都没有,更丢人。
“行,那你给我好好弄弄。”
他交了三百块钱。
车开回来,一股浓烈的柠檬香精味盖住了一切。
老王心里刚一松。
第二天早上,太阳一晒。
那股腐烂的甜腥气,变本加厉地冲破了香精的封锁,喷薄而出。
“王建国!你还进不进门!”
张桂芳站在楼上吼他,他刚从车里出来,张桂芳说他身上带回了味儿。
“你再碰那车,就别上床睡觉!”
老王彻底被激怒了。
这不是车的问题,这是他王建国的尊严问题。
“行!我不睡!”
他红着眼,转身下了楼。
“桂芳,把我的工具箱递下来!”
“你干吗?”
“我拆了它!”老王吼道,“我倒要看看,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死耗子!”
张桂芳看他那股疯劲,也不敢再拦,嘟囔着把那个沉重的铁皮工具箱从窗户递了出来。
家属院的傍晚,邻居们开始遛弯。
所有人都看见,老王提着工具箱,拉开了那辆银灰色面包车的侧门,一头钻了进去。
“老王这是...修车呢?”
“他不是刚从汽修厂回来吗?又坏了?”
老王充耳不闻。
他打开车内所有的灯,刺眼的光线下,灰尘乱飞。
他锁定了目标——第二排右侧座椅。
拆车,老王是专业的。
他先卸掉了座椅底下的四颗固定螺丝。
“嘎吱——” 螺丝刀和金属摩擦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螺丝很紧,有的已经锈住了。
老王憋着一口气,用上了加力扳手。
“砰!”
一颗螺丝崩飞了。
他满头大汗,那股甜腥味混着汗味,熏得他直反胃。
他干脆从后备箱扯了块破毛巾,蘸了点矿泉水,捂住了口鼻。
半个小时后,四个固定螺丝全被卸了下来。
他抓着座椅的底座,使劲往外拖。
“哗啦——”
座椅被整个拖到了车厢中间。
04.
座椅搬离了原来的位置。
老王低头去看地板。
地板上,除了几个螺丝孔,只有一层厚厚的浮土,和几块黏糊糊的、干涸的饮料渍。
“没有?”
老王不死心,他趴下去,把脸贴在地板上。
味道还在。
他猛地抬头,看向那张被拖到中间的座椅。
源头,就在这张椅子里!
邻居老李头遛弯路过,敲了敲车窗。
“建国,拆车呢?你这可别把安全气囊拆爆了。”
“去去去,我心里有数!”老王不耐烦地挥挥手。
他关上车门,把自己和那张座椅锁在狭小的空间里。
那股味道,现在浓烈得几乎成了实体。
老王被熏得眼睛发酸,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他必须速战速决。
他开始拆座椅的蒙布。
这活儿比拆螺丝难。
家用面包车的座椅蒙布,边缘都是用特制的卡扣和缝线固定的。
老王用平口螺丝刀一点点撬开塑料压条,又用钳子去拔那些固定钉。
“嘶啦——”
第一块蒙布被扯开了。
里面是厚厚的海绵。
老王把手电筒凑过去。
海绵是黄色的,很干净,只是边缘有点发黑。
他用手按了按。
“咦?”
他感觉指尖按到的地方,海绵的回弹不对劲。
有的地方软,有的地方...硬。
像是在海绵里面,塞了别的东西。
他顾不上了。
他抄起工具箱里的美工刀。
“王建国!你疯了!”张桂芳在楼上喊,她一直从窗户里盯着,“你把新买的椅子划了?!那还怎么卖!”
“别管我!”
老王屏住呼吸,刀片“噗嗤”一声插进了海绵里。
他横着一拉。
“哗啦!”
黄色的海绵翻开。
海绵下面,不是钢架,而是一层黑色的...塑料布?
不,是垃圾袋。
那种厨房用的,最厚实的黑色垃圾袋,被人用透明胶带,一圈一圈,缠得严严实实。
老王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谁会在座椅海绵里藏一包垃圾?
那股甜腥的腐烂气味,就是从这包东西里透出来的!这股味道,被海绵和蒙布闷了这么久!
05.
车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老王盯着那个黑色的包裹。
它被塞在海绵和座椅弹簧的夹层里,形状很不规则,大概有...两三个小臂那么长。
“什么玩意儿...”
他伸手戳了一下。
软的,但又带着某种韧性,好像里面包着...肉?
是哪个缺德的跑水产的,把不要的鱼肉塞在这了?
他想到了那个被抓走的黄毛销售。
想到了这辆凭空便宜了两万块的车。
他咽了口唾沫,汗毛都立了起来。
“王建国!”
楼上,张桂芳还在喊:“你拆完了没?赶紧上来吃饭!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!”
“...就来!”
老王的声音干涩沙哑。
他不能把这东西拿出车外。
他用美工刀,小心翼翼地,在黑色塑料袋的边缘,划开了一个小口。
“嗤——”
一股无法形容的气体,猛地冲了出来。
老王“哇”的一声,差点吐出来。
这不是死耗子,也不是烂鱼烂虾。
这是...
他不敢想。
他强忍着恶心,把美工刀的刀尖,顺着那个小口,一点点往里探。
刀尖碰到了一个硬物。
他用刀尖拨开层层叠叠的塑料袋。
借着车内刺眼的顶灯,他终于看清了。
塑料袋里,不是一块,而是好几块。
被什么液体泡得发白、发胀。
在其中一块的边缘,他还看到了几个模糊的、蓝紫色的...图案?
像是什么纹身的一部分。
老王的大脑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他当过兵,他知道这是什么。
这不是猪肉,也不是羊肉。
他“砰”地一声摔上了车门,从车里滚了出来。
他靠在车轮上,拼命地喘气,胃里翻江倒海。
家属院的灯光下,他的脸一片煞白。
“老王?你咋了?脸色这么难看?”老李头又转悠回来了。
老王摆摆手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他扶着墙,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。
他摸向口袋。
他的那台老式智能手机,屏幕上还沾着刚才拆车时的油污。
他划开屏幕,手指哆哆嗦嗦地,怎么也点不准那几个数字。
试了三次。
终于。
他手抖着拨了110。
“喂...喂...警察吗?”
“我在...我在钢厂家属院...”
“我买了辆车...车里...车里有...”
他看着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,它安静地停在夜色里,像一头沉默的怪兽。
“车里...有死人!”
06.
“喂...车里...有死人!”
王建国的声音在发抖,几乎握不住手机。
“你别动现场!别碰任何东西!我们马上到!” 电话那头的声音冷静而威严。
“老王!你喊什么死人!你疯了!” 张桂芳从楼上冲下来,一把抓住他的胳膊,“你是不是拆车拆魔怔了?”
老王指着那辆面包车,嘴唇发白:“里面...真的...我看到了...”
话音未落,远处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。
由远及近,不到五分钟,两辆警车闪着红蓝光,呼啸着冲进了老旧的钢厂家属院。
这一下,整个家属院都被惊动了。
“怎么回事?老王家出什么事了?”
“警察都来了!动静这么大?”
邻居们披着衣服,从各个单元门里涌出来,瞬间围了一圈。
车门打开,走下来几名警察。为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警官,国字脸,眼神锐利。
“谁报的警?”
“我...是我...” 老王举起手,他的腿还在软。
“我是市刑侦支队的队长,李建军。” 李队长看了老王一眼,“你就是王建国?车是你的?”
“是...我刚买的二手车...”
“你发现了什么?”
老王指着那扇开着门的面包车,喉咙发干:“在...在第二排座椅的夹层里...我拆开了...有...有个黑塑料袋...”
李队长一挥手,两名穿着勘查服的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上前,拉起了警戒线。
“所有人!退后!保护现场!”
聚光灯亮起,刺眼的光照在那辆银灰色面包车上。
邻居们这才看清老王脚边的工具——扳手、钳子、还有那把带着血污的美工刀。
人群“嗡”的一声炸开了。
“天呐!老王杀人了?!”
“胡说什么!老王是说车里有东西!”
“他图便宜买的那车...我就说不对劲!”
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扎向老王。
张桂芳的脸“唰”一下白了,但她猛地站直了身子,挡在老王身前,冲着邻居们喊:“都别瞎说!我家老王是受害者!他要是心里有鬼,他会自己报警?!”
这一声怒吼,暂时压住了议论。
李队长看了张桂芳一眼,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。
技术人员钻进车里,很快,他们抬出了一个沉重的、密封的物证箱。
“李队,”一个年轻法医走过来,脸色凝重,“初步确认,是人体组织碎块,腐败程度很高。现场...很干净,像是被专业清理过。”
李队长的眉头锁紧了。
他转向王建国:“王师傅,从现在开始,这辆车是重要物证,我们要拖走。你,还有你爱人,需要跟我们回局里,详细做一个笔录。”
“李队长,” 老王哆哆嗦嗦地问,“这...这到底怎么回事?我...我就是图个便宜...”
“你现在不用想别的。” 李队长的声音很沉稳,“你做的很对。你第一时间报警,保护了现场,给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。”
“王师傅,” 他拍了拍老王的肩膀,“别怕。你不是嫌疑人,你是这个案子的...第一功臣。”
07.
市局的灯亮了一夜。
老王和张桂芳被分开询问。
老王不愧是老机修工,他把自己买车的每一个细节,从黄毛销售的表情,到合同上的每一个字,再到他这几天闻到的味道变化,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“我就是不服气,” 老王攥着拳头,“我王建国一辈子没看走眼过,这次...我非要把它拆开看看!”
另一边,张桂芳把家里的情况、老王的退休金、孙子的抱怨,也都说了。
“警察同志,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。这车...我们花了七万块!那是我家老王大半辈子的积蓄啊...” 她说着说着,眼泪就下来了,“这钱...还能要回来吗?”
负责笔录的年轻警察安慰道:“阿姨,钱的事情我们后续会处理,现在最重要的是破案。你们提供的线索非常关键。”
凌晨四点,老王和张桂芳被送回了家属院。
警车走了,但家属院的天,还没亮。
两口子坐在客厅,谁也睡不着。
“老王...你...你没看错吧?”
“看错了?那味道能错吗!那...那纹身...” 老王捂着脸,胃里又是一阵翻腾。
接下来的几天,老王家成了家属院的中心。
有来安慰的,有来看热闹的,更多的是来打听“内幕消息”的。
老王一概不说。他被李队长叮嘱过,案件侦破期间,要保密。
张桂芳也一反常态,不再骂人,谁来问,她就一句话:“等警方通告。”
老王一辈子的“面子”,这次换了一种方式回来了。
他不再是“贪便宜买破车”的笑话,而是“胆大心细协助警方”的英雄。
第七天,李队长亲自登门了。
他给老王带了两条烟。
“王师傅,张阿姨,案子有重大突破。”
李队长喝了口水,表情严肃:“我们通过你说的那个纹身,结合近期待失踪人口库,确认了受害者。”
“受害人,名叫阿辉,28岁,外地人,没有正当职业。”
“他...怎么死的?”张桂芳小声问。
“这就是关键。”李队长说,“我们顺着你提供的二手车市场线索,抓到了那个‘黄毛’。他全招了。”
“黄毛”叫小黄,是个专卖“黑车”、“抵押车”的二道贩子。
据小黄交代,这辆车,是十天前一个自称姓胡的男人开来的。
“那人急着出手,戴着口罩帽子,说车是抵押来的,手续不全,让我赶紧处理掉。价格压得特别低。”小黄说。
“我寻思这车况好,就收了。可收了才发现,味儿不对。我用香水、臭氧机都试了,盖不住。正愁呢,你家老王就来了...”
“老王师傅,” 李队长看着老王,“你当时看车那么仔细,小黄说他紧张得要死,生怕你发现什么。结果你只说了句‘香水味浓了点’,他以为你没闻出来,就赶紧忽悠你买下了。”
老王老脸一红:“我...我以为是前车主爱干净...”
“这个姓胡的,有重大嫌疑。”李队长说,“但我们查了监控,他是套牌车来的,留的电话也是假的。线索,到‘黄毛’这里,几乎断了。”
08.
线索一断,案子就陷入了僵局。
受害人阿辉社会关系复杂,仇家很多。而那个“胡姓男子”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
家属院的议论又起来了。
“我就说,那车就是个凶车,老王倒了血霉了。”
“这案子怕是要悬了,杀人犯多精啊。”
老王心里也憋着一口气。他天天看新闻,就等警方的通报。
这天晚上,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“桂芳,你说...我是不是漏了什么?”
“你都跟警察说了三遍了,还能漏什么?”
“不对...” 老王猛地坐了起来,“不对!”
他披上衣服,冲到阳台,把他那个沾满油污的工具箱拖了进来。
“你干吗!大半夜的!”
老王不说话,把工具箱里的东西“哗啦”一下全倒在地板上。
扳手、螺丝刀、套筒...滚了一地。
他在零件堆里扒拉着。
“找到了!”
他捏起一个黑乎乎、皱巴巴的东西,像是一团废纸。
“这是什么?”张桂芳凑过去。
“我拆车那天...” 老王眼睛放光,“我不光拆了座椅,我还检查了发动机舱!我这老本行,丢不掉!我当时打开了空滤盒子,想看看滤芯脏不脏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就在空滤盒子的角落里,塞着这个!”
老王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团东西。
那是一张高级餐厅的停车小票,已经被机油浸透了一半,但上面的日期和时间,依稀可见。
“12月5号,晚上8点,金海湾大酒楼。”
“我当时以为是前车主随手扔的垃圾,就团了揣兜里,后来就扔进工具箱了...我忘了跟李队说!”
“这有什么用?”
“用处大了!”老王激动得手抖,“空滤盒子!那是藏东西的地方吗?正常人谁会把小票塞那儿?这说明,是有人故意藏的!而且,这个日期...我查了,就是那小子‘黄毛’收车的前两天!”
他立刻拨通了李队长的电话。
09.
半小时后,李队长带着两名技术员再次登门。
当他戴上手套,接过那张油腻腻的停车小票时,他这位老刑警的眼睛也亮了。
“王师傅!你立了大功了!”
“金海湾大酒楼...” 李队长喃喃道,“12月5号晚8点...立刻调取那天晚上酒楼周边的所有监控!”
突破口,就在这张被遗忘的小票上。
第二天天刚亮,好消息就传来了。
监控调出来了。
12月5号晚上8点03分,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,准时出现在了金海湾大酒楼的停车场。
车上下来两个人。
一个是受害人阿辉。
另一个,正是那个“胡姓男子”!
这一次,他没戴口罩。
“人脸识别系统对上了!” 李队长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兴奋,“嫌疑人胡某,42岁,本地人。和受害人阿辉有共同的非法放贷记录!”
抓捕行动雷霆万钧。
当天下午,正在另一家二手车市场准备故技重施、处理掉自己另一辆“问题车”的胡某,被警方当场按住。
证据链瞬间闭合了。
胡某和阿辉是“合伙人”,因为分赃不均,胡某动了杀心。
他约阿辉在“金海湾”吃饭,假装和解。在车上,他趁阿辉不备,将其杀害。
他深知这辆车脱不了干系,便连夜将尸体处理,藏在座椅夹层中,打算等风头过了再抛尸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,那股味道怎么也除不掉。
他更没想到,自己慌乱中藏在空滤盒子里、用以伪造不在场证明的停车票,忘拿了。
他最最没想到的是,这辆车,会卖给一个“图便宜”的退休老机修工。
一个会因为一股味道,就把整张椅子拆散架的“犟种”老师傅。
案件侦破的消息,由市局官方公众号发布。
通告里,特别提到了“家属院退休职工王建国同志,在发现可疑情况后,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了关键线索”。
王建国,成了家属院的英雄。
10.
半年后。
胡某被依法判处了死刑,法律给了受害人阿辉一个公正的交代。
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,在结案后,被发还给了王建国。
车被清理得干干净净,那张被划破的座椅也由警方修复了。但它静静地停在楼下,还是显得有些刺眼。
“老王,这车...还开吗?”张桂芳问。
“开,怎么不开。”
老王沉默地忙活了一个星期。
他没有再开那辆车去接孙子。
他把车开到了汽修厂,自费,把车里所有的内饰、座椅、地胶,全都换了新的。
焕然一新,再也没有一丝异味。
张桂芳以为他要高价卖掉,挽回点损失。
“老王,这回可不能图便宜了啊!”
老王笑了笑,没说话。
又过了一周,一个周六。
老王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一件夹克,把车擦得锃亮。
他载着张桂芳,开到了市郊的一个“春蕾助学基金会”。
在张桂芳惊讶的目光中,老王找到了负责人,签署了捐赠协议。
“王师傅,您这车...我们评估过了,至少还值五万多,您真的...就这么捐了?”负责人再三确认。
“捐!”老王签字的手,稳稳当当,“这车,我们家留着,心里膈应。但车是好车,发动机好着呢。你们拿去,给山区的老师们送教具、接孩子,它才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。”
“那...受害人阿辉...” 张桂芳还是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。
老王拉着她,走到了基金会旁边的江边。
他拿出一瓶白酒,拧开,洒向江面。
“小伙子,” 他对着江水说,“你的冤屈报了。这车,也算替你积德了。安心去吧。”
捐赠仪式很简单。
基金会给老王和张桂芳颁发了一面锦旗。
“王建国、张桂芳夫妇:大爱无疆,义举感人。”
回家的路上,两人是坐公交车回来的。
家属院的夕阳下,邻居们正在遛弯。
“老王,车呢?卖啦?”
“捐了!”张桂芳抢着说,把锦旗高高举起。
没人再提那件凶案,也没人再笑话老王图便宜。
所有的目光,都变成了尊敬。
老王背着手,胸脯挺得笔直,这辈子都没这么“有面子”过。
“桂芳,” 他清了清嗓子。
“干吗?”
“明天...咱俩去4S店。”
“又买?!”
“买!”老王大手一挥,“这回...买新的!你挑!咱孙子,也该坐坐新车了!”

